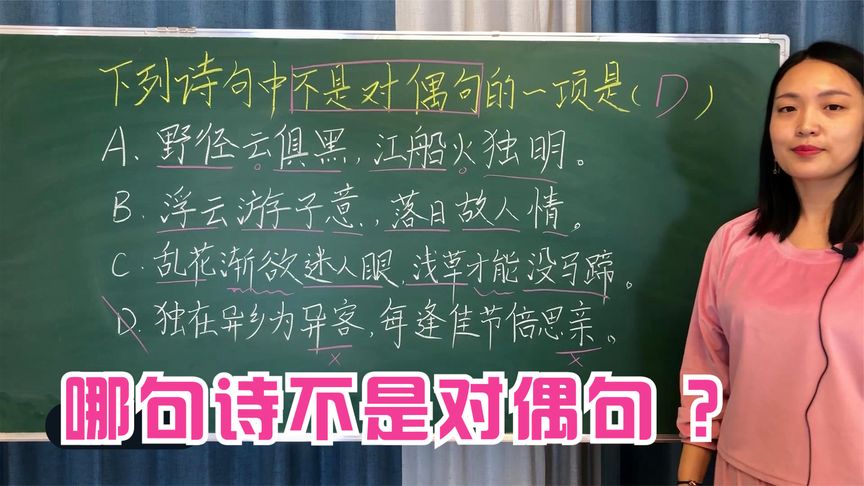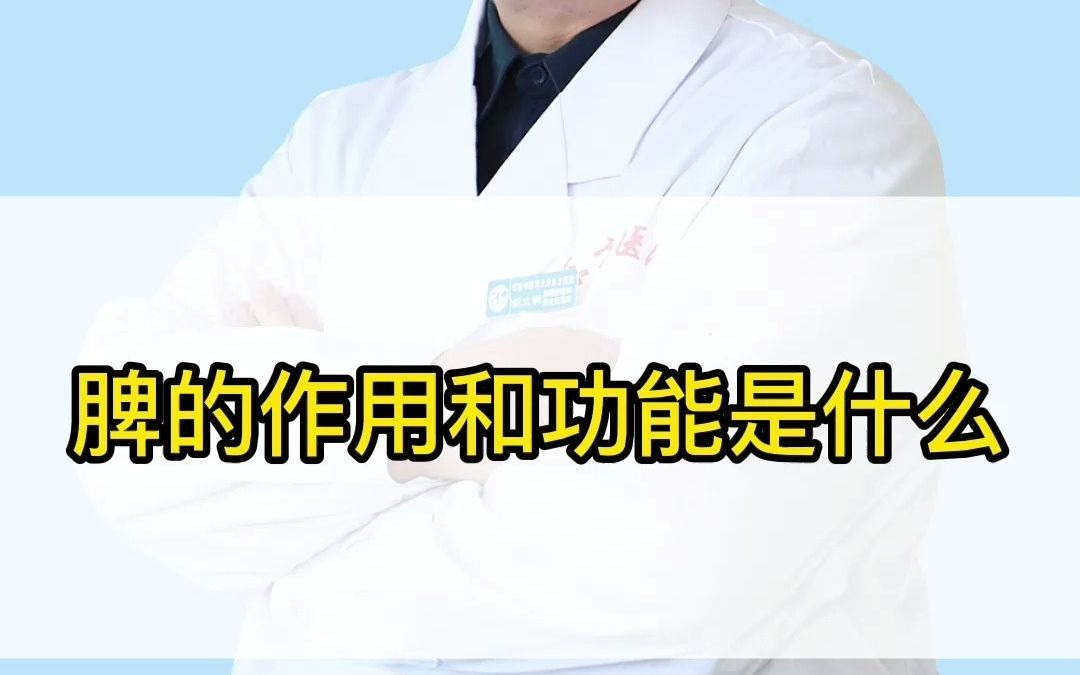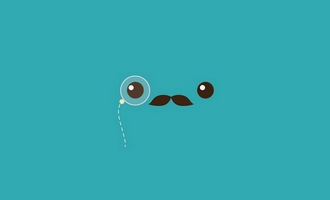“疚”字为“病”字旁,代表痛苦;内部的“久”代表持久。“疚”的本义是“久病”,如《韩非子》中“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”中的“疚”字,意思就是久病。尽管“久病”的字面意义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,但它的衍生意义依然存在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疚”字的解释是“对于自己的错误感到内心痛苦”。可见,这个词如今只用来表示因自己的错误、过失而在内心放不下,产生持久的痛苦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中国人对自己要求高,在自己犯错误后可能会有持久的痛苦,且这痛苦就是“持久的心病”。
“疚”字可以和其他意义相近的词结合,构成愧疚、歉疚等词。愧疚,是因为有愧而内疚;歉疚,是因为抱歉而内疚。这里的“愧”“歉”都说明了这个人感觉负疚的原因。之所以会心生内疚,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而给别人带来了损失或伤害,即所谓的“对不起别人”。这里所说的“错误”,既可能是过失性的(比如,因开车时不小心而撞伤了人),又可能是蓄意的(比如,在升职竞争中,因一时没管住自己而散布谣言、打击对手)。需要注意的是,产生内疚感的关键来自自我内心的评价——并非事实上是否对不起人,而是自认为是否对不起人。有的人在事实上对别人造成了严重伤害,很可能会认为“我没有过错,都是他活该”;相反,有的人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别人,却可能会因为他自认为伤害了别人而觉得“对不起别人”。
内疚时在身体上的反应主要集中于胸区,是一种心口附近缩起来、心抽紧了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可能会让人把双手抱在胸前,好像手臂也被连带着抽紧了似的。在抽得格外紧的时候,胸口也会感到痛,并感到一种向背部方向的压力,好像会把胸压得瘪下去。胸口这样紧缩,呼吸就不顺畅,所以人在内疚时会感到胸口发闷、喘不过气来。还有一种反应是头会低下去,肩也会向前弯一些,形成类似鞠躬的动作。手脚还可能会变得无力或“不敢用力”(即手不敢用力动或脚不敢用力踩在地上),就像怕手脚再一次做出坏事一样。
如果内疚感更加严重,人可能就会因严厉的自责而捶打自己的胸区或头部——这是在以自我伤害的方式来“偿还”对别人的伤害。如果内疚感极为严重,就会变成所谓的“罪疚感”——此时人的膝盖还会不由自主地跪下,就好像本能地要表达谢罪之情一样;还可能会用狠狠地扇自己耳光、重重地在硬地上或硬墙上连续磕头、自割、自残等更严重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来宣泄和表达罪疚感。
内疚时,意象中最容易出现的是自己所伤害之人的痛苦的象征性意象,有时还会出现作为加害者的自己冷漠无情或卑鄙的样子——人在意象中往往会夸大自己的坏。例如,如果因自己在现实中拒绝了他人的求助而心生内疚,那么在意象中,对方也许会变形为一个可怜的小孩子,在冰天雪地中求搭车,自己则是一个冷漠的成年人,不理不睬地开车离开,让那个小孩子颤抖着在冰雪中等死。内疚的意象还常常以谢罪者的姿态出现,比如,一个人跪在冰天雪地里自我责罚,或是跪在受害者面前的地上把头磕出血等。内疚的感觉很不好受,因此人会急于消除它。
消除内疚感有以下五种常见的方式。
第一种方式是最有效、最健康的——向受害者忏悔,并给予受害者补偿。一旦看到对方因此得到了获益并且不再痛苦了,自己的内疚之苦就可以随之减弱了;如果受害者是个善良的人,愿意原谅自己,那么自己的内疚感甚至可以消退。
第二种方式是归咎于人,也就是否认自己伤害了对方,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,说那个所谓“受害者”的痛苦完全不怪自己,而是他自己的错,或是别人的错。如果这个人的确有错,那么这种方法只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,无法真正解决问题。而且归咎于人的这种行为,反而会带来新的伤害。有的使用这种策略的人甚至还会诋毁、陷害受害者,把受害者在公众面前妖魔化,更加激烈地加害对方,从而试图让自己和别人都相信,自己才是那个有权去“复仇”的“受害者”。
第三种方式是自我惩罚。采用这种方式的人没有勇气去面对被自己伤害的人,所以无法在现实中给予受害者真正的补偿,只能暗地里责罚自己作为替代性的补偿。这样就能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个“杀人偿命”的交代,就好像说:“是的,我以前伤害了你,但是现在我已经连本带利地伤害了自己,我替你报仇了。现在我已经刑满出狱了,我可以重获自由,不再歉疚了。”
第四种方式是自我麻醉,即让自己变得没心没肺,从而对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没什么感觉,甚至彻底让自己忘记自己对不起别人的事。这种方式只能在意识层起到一定的缓解内疚的作用,一旦午夜梦回,被暂时从意识域屏蔽出去的那些记忆和感受就会卷土重来,以更加强烈的方式反扑,给自己带来更严重、更持久的心理折磨。
第五种方式是索性自暴自弃,向加害者表示认同,即对自己说:“对呀,我就是要伤害别人!因为我就是恶人!我偏偏就是喜欢这样、享受这样,怎么着?!”这种方式是最危险的,不但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多的伤害,还会危害社会,更会对其自身的心理健康带来毁灭性的打击,因为这种处理方式等同于杀死了自己心中尚有良知的人性自我。
多数孩子在三岁之前很少能产生内疚感,因为在此之前,孩子的自我(ego)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,缺乏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,也就难以知道别人的痛苦是什么样子的。不知道别人的痛苦,就不会懂得内疚。内疚能力其实是人理解他人的能力,以及通过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避免让别人痛苦的能力,是一种对社会生活很有用的能力。儒家所说的君子“内省不疚”,就是指君子能够不伤害其他人,从而在内省中不会产生内疚感。
在俄狄浦斯期,父母的行为方式会影响孩子内疚感的形成。有的父母心理不够健康,会无意识地强化孩子的内疚感,以作为控制孩子的一种心理策略——让孩子感到内疚,孩子就会听话,自愿在情感上付出。这种控制孩子的心理策略被称为“内疚控制”。在儿时被内疚控制的孩子,日后会过度自我牺牲、过度顺从别人,在情感上被别人剥削,成为受害者。有些被内疚控制的人,还会形成对别人内疚控制的习惯。他们会夸大自己的受害或是表演被害,甚至会对亲近的人进行被动攻击,用种种言行向别人暗示自己被亲近的人伤害了。这样一来,他们就强化了身边亲近的人的内疚感,从而控制他们。在我们的生活中,这种人大有人在。
有良心的人在做错事的时候都会内疚,他们会在内疚感的驱动下做一些补救或是有补偿性的事情,以减少自己造成的损失。这种正常的内疚不仅是无害的,还是有益的。然而,如果是被内疚控制而产生的内疚感则是不合理的、病态的,需要改变。在心理咨询中,如果来访者有这种病态的内疚,咨询师就要帮助他进行自我观察。来访者在深入、认真地自我观察之后会发现,在那些令其内疚的事情中,他也许并没有做错什么,或是虽然有过失,但是过失并不大,并不应该那么内疚。来访者随后还可能会看到,是谁在对自己进行内疚控制。在看清了这一点后,他就可以去做耐受自己习惯性产生的内疚感的训练,但是不要做出自我牺牲的事情(即不要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强化别人的内疚控制)。经过长期训练之后,来访者就可以慢慢地脱离被别人内疚控制的魔咒了。
还有一种人很习惯过度内疚。比如,他会因为自己某一次对某人说了一句有情绪的话,在后续每次见到对方时都会很隆重地向对方道歉,而对方可能早已忘记了这件事。再如,有一位邻居跳楼了,他会因自己没能做点什么去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内疚,他会痛苦地想:“上个月我就发现她有些不对劲了,为什么那时我没去及时和她聊聊呢?如果我能说服她去精神科看看,也许她就能发现自己得了抑郁症并得到及时治疗。唉!她的死有我的一份责任啊!”如果我们为他做心理分析,就很可能会发现,在他过度体现的良心背后隐藏着强烈的自恋——他的潜意识仿佛一直在沾沾自喜地看着自己赞叹说“我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”“我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”“我有能力改变别人的命运”“如果我愿意,我甚至能决定别人的生死”之类的。
顺便说一句,英语中的“guilt”常被翻译成“内疚”,但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与中国文化中的“内疚”是有区别的。“guilt”的意思,与其说是“内疚”,不如说是“负罪感”,是指感到自己“有罪”。然而,基督教文化中讲的“有罪”与中国文化中“有过失”并不是一回事。中国文化认为“有过失”不是必然的,我们可能犯错,也可能不犯;基督教文化则认为,人天生有罪(即原罪),所以不可能不“有罪”。因此,“guilt”并不包含这种“我怎么能做这样的错事或坏事呢”的感觉,因为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有罪,不可能不做坏事,是一种“我知道我是罪人,没有办法”的感觉。“guilt”并不导向补偿受害者,因为即使补偿了受害者也没有什么用处,补偿了受害者也改变不了自己是“罪人”。“guilt”的应对方法,只能是向上帝认罪,承认自己是天生有罪的,求上帝宽恕自己。以上我所说的关于内疚的内容,都是指中国文化中的“内疚”,而不是关于“guilt”的。